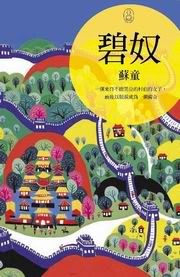
起始˙重寫「神話」?
剛開始,聽到參加了重述神話此一計畫的中國作家蘇童要改寫的是孟姜女的故事,我心中暗暗吃了一驚--孟姜女哭倒長城,這個故事(或者該說是詞條)對我來說,遠遠搆不上「神話」的邊。這個故事之中沒有神,有的只是在往後千年中不斷重複出現的暴君、徭役與女子。說它是神話,倒不如說更接近民間故事的「人話」。然而或者也因此更讓我好奇於蘇童如何重寫?如何將這個「民話」改變成為「神話」?
蘇童沒有。他保持了原有的民話特質。《碧奴》實質上是一場漫長的公路旅行,而途中,「神」在此銷聲匿跡(對於「靈」,倒是有不少的描寫。),而「神話」的意義,或許在敬鬼神而遠之的儒家文化與堅守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夾擊下,似乎終於如同「資本主義」一般,轉化為「中國脈絡下」獨有的語境。
開場˙「淚」的傳奇
孟姜女/碧奴的傳奇,與其說是她的傳奇,倒不如說是淚的傳奇。淚,作為身心面臨悲傷時的象徵,在一代代流傳的孟姜傳說中逐漸發展出了驚天動地的力量。淚擊潰了長城,猶如個人意志不可思議的擊潰了國家機器。而這樣的意志從何而來?是什麼樣的意志得以造就如此的成果?
因而蘇童給了碧奴一個桃村(逃村?)身世。桃村的人曾經因哭獲罪,死傷大半,因而村中人視哭為禁忌--淚水可以流,可以自各式各樣的身體器官中流出,就是不能從眼中流,流了,就得死了--這其實是挺典型的傳說生成方式:集體的歷史記憶幻化為某個莫名其妙的禁忌,而不明所以的後人在傳達禁忌時,便順帶的以身體繼承了那些慘痛記憶。這也是碧奴其後在百春臺的林子中以為自己會死,卻遲遲等不到死神的原因。蘇童巧妙的揉雜了真實的傳說生成方式於魔幻書寫之中,於是營造出既荒誕又合理的橋段(而這,難道不正是我們在解讀傳說時所會感受到的嗎?)
路途˙行路難--萬里迢迢的公路旅行
孟姜女/碧奴的旅程雖然漫長,然而在被傳述的過程中卻總是被輕描淡寫的帶過。「遠走千里」四個字,之中蘊含了多少時光乃至於艱辛。而一個窮困的女子孤身上路,一路上又會遭遇到多少人事物?需要多少的勇氣與堅持?她會不會心灰意冷?會不會想反轉回家?
碧奴遇到了很多人很多事,很多艱辛乃至於汙辱。然而屬於她個人的意志,卻是從頭到尾的「我要到大燕嶺去!」這樣一種近乎著魔的堅持,幾乎沒有身為一個「人」所會有的膽小、後悔、不安等等輾轉反側,而是一無反顧的堅持--這可是連最近的英雄都做不到的事情--無怪乎論者會認為碧奴是個「個性憨直但固執近冥頑、有過人體力卻沒有及格腦力」的人物,而讀者則紛紛認為她「堅貞的過於愚蠢」。
而我則覺得,這故事的主角或許根本不是碧奴。碧奴僅僅是一個載體,如同文字承載了意志般,碧奴承載了淚。一路上的片片段段,是為了讓碧奴的身上不斷的積蓄更多更多的淚水:大牲口的淚、馬人鹿人的淚、刺客的淚、販夫走卒的淚......
淚,作為真正的主角,實際上則是一直在「成長」的。桃村的女子學會了各式各樣的哭泣。自手、自髮、自胸、自耳。碧奴亦然。然而碧奴她娘死的早,沒來得及教會她除了用髮哭以外的方法。然而,在踏上這場旅程之後,「淚」,或者說哭的方法,開始一樣樣的在碧奴身上「覺醒」。碧奴學會了用身上的各種孔竅、各式器官哭泣,學會了哭出五味淚(又或者,是淚開始有所自覺,開始懂得酸甜鹹苦辣?)而碧奴的淚,最終呼朋引伴的招來了萬千尋子的青蛙婦人,招來了萬千尋夫的採桑妻女,招來了萬千尋後的遙遠祖靈,最終成為千萬身軀的民間哭號,翻倒了牆,挖出了萬豈粱。
而碧奴作為載體,所承載的也就成了這整個民間--這甚至可追溯到傳統的男性為陽,女性為陰敘事框架下,皇帝是陽性,臣子為陰性;官方為陽性,民間為陰性等等的強/弱權力結構。於是,官府的橫徵暴歛是碧奴受苦的根源,而民間--人民之間的傾軋爭鬥,成了碧奴受苦的旅程。碧奴的自虐與他虐,實際上便是整個民間的自虐與他虐。而若將「送冬衣給萬豈粱」(相互取暖)視為碧奴的夢想,那麼碧奴尋夫的旅程,實際上便是一場追尋希望的旅程--只是不同於潘朵拉之盒,碧奴的希望早已埋葬在權力之下。
而推倒城牆就能重獲希望嗎?
萬豈梁依舊死了。而城牆,依舊存在。
尾聲˙一些微小的問題
我不曉得蘇童是否有意藉由拼貼歷史符碼而得到一個不僅僅是秦朝的中國民間,因小說中的刺史為唐朝官名,而也論及到儒家思想(就歷史觀點來看,儒家成為「國教」也是漢武之後的事了)。背景有些模糊,事件卻又歷歷可辨--或許《碧奴》的背景是我們這個歷史的某種轉世,一如碧奴相信她是葫蘆命:重視入土為安,離鄉之前要先種下自己的來世。這樣的命格,或許也正是熟知中國人性格的蘇童所預先安排的吧?
最後當然免不了期許了。這個重述神話的計畫是個向國際宣傳本土作家的好機會,畢竟有那麼多種語言的譯本。未知是否有出版社能替/正在替臺灣的作家爭取出版的機會?
[emoji:i-220]延伸閱讀:
穿著小說外衣的孟姜女/賀淑瑋
苏童在《碧奴》里犯错
孟姜女/碧奴的傳奇,與其說是她的傳奇,倒不如說是淚的傳奇。淚,作為身心面臨悲傷時的象徵,在一代代流傳的孟姜傳說中逐漸發展出了驚天動地的力量。淚擊潰了長城,猶如個人意志不可思議的擊潰了國家機器。而這樣的意志從何而來?是什麼樣的意志得以造就如此的成果?
因而蘇童給了碧奴一個桃村(逃村?)身世。桃村的人曾經因哭獲罪,死傷大半,因而村中人視哭為禁忌--淚水可以流,可以自各式各樣的身體器官中流出,就是不能從眼中流,流了,就得死了--這其實是挺典型的傳說生成方式:集體的歷史記憶幻化為某個莫名其妙的禁忌,而不明所以的後人在傳達禁忌時,便順帶的以身體繼承了那些慘痛記憶。這也是碧奴其後在百春臺的林子中以為自己會死,卻遲遲等不到死神的原因。蘇童巧妙的揉雜了真實的傳說生成方式於魔幻書寫之中,於是營造出既荒誕又合理的橋段(而這,難道不正是我們在解讀傳說時所會感受到的嗎?)
路途˙行路難--萬里迢迢的公路旅行
孟姜女/碧奴的旅程雖然漫長,然而在被傳述的過程中卻總是被輕描淡寫的帶過。「遠走千里」四個字,之中蘊含了多少時光乃至於艱辛。而一個窮困的女子孤身上路,一路上又會遭遇到多少人事物?需要多少的勇氣與堅持?她會不會心灰意冷?會不會想反轉回家?
碧奴遇到了很多人很多事,很多艱辛乃至於汙辱。然而屬於她個人的意志,卻是從頭到尾的「我要到大燕嶺去!」這樣一種近乎著魔的堅持,幾乎沒有身為一個「人」所會有的膽小、後悔、不安等等輾轉反側,而是一無反顧的堅持--這可是連最近的英雄都做不到的事情--無怪乎論者會認為碧奴是個「個性憨直但固執近冥頑、有過人體力卻沒有及格腦力」的人物,而讀者則紛紛認為她「堅貞的過於愚蠢」。
而我則覺得,這故事的主角或許根本不是碧奴。碧奴僅僅是一個載體,如同文字承載了意志般,碧奴承載了淚。一路上的片片段段,是為了讓碧奴的身上不斷的積蓄更多更多的淚水:大牲口的淚、馬人鹿人的淚、刺客的淚、販夫走卒的淚......
淚,作為真正的主角,實際上則是一直在「成長」的。桃村的女子學會了各式各樣的哭泣。自手、自髮、自胸、自耳。碧奴亦然。然而碧奴她娘死的早,沒來得及教會她除了用髮哭以外的方法。然而,在踏上這場旅程之後,「淚」,或者說哭的方法,開始一樣樣的在碧奴身上「覺醒」。碧奴學會了用身上的各種孔竅、各式器官哭泣,學會了哭出五味淚(又或者,是淚開始有所自覺,開始懂得酸甜鹹苦辣?)而碧奴的淚,最終呼朋引伴的招來了萬千尋子的青蛙婦人,招來了萬千尋夫的採桑妻女,招來了萬千尋後的遙遠祖靈,最終成為千萬身軀的民間哭號,翻倒了牆,挖出了萬豈粱。
而碧奴作為載體,所承載的也就成了這整個民間--這甚至可追溯到傳統的男性為陽,女性為陰敘事框架下,皇帝是陽性,臣子為陰性;官方為陽性,民間為陰性等等的強/弱權力結構。於是,官府的橫徵暴歛是碧奴受苦的根源,而民間--人民之間的傾軋爭鬥,成了碧奴受苦的旅程。碧奴的自虐與他虐,實際上便是整個民間的自虐與他虐。而若將「送冬衣給萬豈粱」(相互取暖)視為碧奴的夢想,那麼碧奴尋夫的旅程,實際上便是一場追尋希望的旅程--只是不同於潘朵拉之盒,碧奴的希望早已埋葬在權力之下。
而推倒城牆就能重獲希望嗎?
萬豈梁依舊死了。而城牆,依舊存在。
尾聲˙一些微小的問題
我不曉得蘇童是否有意藉由拼貼歷史符碼而得到一個不僅僅是秦朝的中國民間,因小說中的刺史為唐朝官名,而也論及到儒家思想(就歷史觀點來看,儒家成為「國教」也是漢武之後的事了)。背景有些模糊,事件卻又歷歷可辨--或許《碧奴》的背景是我們這個歷史的某種轉世,一如碧奴相信她是葫蘆命:重視入土為安,離鄉之前要先種下自己的來世。這樣的命格,或許也正是熟知中國人性格的蘇童所預先安排的吧?
最後當然免不了期許了。這個重述神話的計畫是個向國際宣傳本土作家的好機會,畢竟有那麼多種語言的譯本。未知是否有出版社能替/正在替臺灣的作家爭取出版的機會?
[emoji:i-220]延伸閱讀:
穿著小說外衣的孟姜女/賀淑瑋
苏童在《碧奴》里犯错
聽說葉兆言、李銳等後來也參加了這個計畫,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在以後幾期的華文選書中讀囉:p

0 意見:
張貼留言